作者:乔忠延(山西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)
共庆中国年,欢乐千万家。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从腊八拉开大年的帷幕,到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“过小年”;从除夕夜阖家团圆守岁,到正月初一亲族邻里拜年……大年,是中华儿女除旧布新、憧憬未来的团圆节、喜庆节。
又一个传统大年如约而至。值此辞旧迎新之际,让我们一起溯源中国年中蕴含的历史根脉、文化内涵。
一
初晓人事,最巴望的莫过于大年,最害怕的也莫过于大年。我幼小的心灵常在矛盾中纠结,既巴望大年早来,因为能吃好饭菜,能穿新衣服,还能挣几角压岁钱;又害怕大年到来,除夕要守岁,不能打瞌睡,要努力克制不闭眼睛,以免被年吃掉。父亲、母亲,还有很多大人都说,年是一个凶恶的野兽。这恶兽凶猛像豺狼,嘴大如血盆,每逢除夕便悄悄蹿进村里,看见哪个小孩睡着了,就一口吞下去。
为驱除我们的恐惧,家家都预备好一挂大红纸包裹的鞭炮。几乎没有小孩不喜欢放鞭炮,点一个,啪地炸响在半空;点一串,噼噼啪啪照亮了夜晚。小伙伴们高兴却说不出来,只会欢蹦乱跳。为啥放鞭炮?吓唬驱赶猛兽。父亲曾说,很早很早以前没有鞭炮,先民砍一大堆竹子,点燃大火,烧得爆裂开来,噼里啪啦炸响,吓得年兽仓皇逃走,这才能平安过年。唐代张说诗句“桃枝堪辟恶,爆竹好惊眠”,宋代王安石诗中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,都道出中国人早就有过年放鞭炮的习俗传统。
随着年岁增长,蓦然悟出,年是时光,是日出日落,是昼夜交替。年,并不意味着“吃人”,而是给人生命,助人成长,教人珍惜时光。想想古人所说的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,想想唐诗所写的“劝君莫惜金缕衣,劝君惜取少年时”,不都是教人珍惜时光、莫负年华的告诫吗?
二
百节年为首,四季春为先。
在所有的节日里,大年排在首位;在四季当中,春季打头先行。一句大白话,道明了国人对大年、对春季是何等重视。这里面包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,甚至更久远的文明积淀。触摸其原点,必须将目光投向狩猎向农耕过渡的时段。
先民纯粹靠狩猎吃饭的时期是没有年的,只有头顶升起落下的太阳和月亮,也就是日和月。日是太阳,升起落下是一个白天;月是月亮,升起落下是一个夜晚。年、月、日是国人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,但你却未必知道,年、月、日最初出现,就是中国历法的开端。在历法中,月不再单纯是月亮,而是代表着一年分为12个段落,月是其中的一个段落。日和月这自然天象,被先祖赋予了新的使命,担当起划分时间秩序的重任。至于年,那可不是自然天象,也不是地理物候,而是先祖用自己的思维判定和划分出的天象认知。有人称之为人文天象,也就是天文。
年的出现,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,标志着中华先祖开始疏远狩猎觅食,步入耕田而食的日子。别看几行字就表述了这划时代的跨越,我们的先祖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。从考古发现看,在南方距今约11000年至8500年的浙江上山文化遗址,已经有了栽培稻;在北方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,已经有了储藏量很大的粟谷。可见,先民早就把采摘果实,发展为种植取食,启动了农耕文明。
然而,数千年间先民们单纯依靠种植还填不满肚子,维生手段一直徘徊在狩猎和农耕之间。一个重要原因,在于先民们不懂天象,无法依据天时下种。先民们的下种时间,要么过早,刚刚出土的禾苗遭受寒霜侵袭,就会冻死,有种无收;要么过迟,果实还在生长,气温骤降,冻瘪籽粒,广种薄收。农耕长期处于低产状态。无疑,天象是制约农耕种植、丰衣足食的瓶颈。
好在,先祖们经过数千年的探索,终于突破了这个瓶颈。突破的标志是有了古朴的历法。不过,在历法中最早露脸的不是年,而是岁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:“帝曰:‘咨!汝羲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,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。’”岁,演变为年,像黄河流水那般,不少于九十九道湾。《尔雅·释天》中记载:“夏曰岁,商曰祀,周曰年,唐虞曰载。”夏禹时期称“岁”,尧舜时期则称“载”,《尚书·尧典》中就有帝尧的一句话:“朕在位七十载。”“周曰年”,《尔雅·释天》提示我们,岁演变为年是在周代。周代以前的商代称作祀。祀是祭祀,下面再说。据考证,甲骨文中出现了“年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对于“年”字的解释是:“谷孰也。”孰,即熟,粟谷成熟的意思。“熟”字的初始象形,犹如一个人背着收获的粟谷。这倒有些像我的少年时代,肩膀还嫩,夏秋农忙挑不起两个禾捆,只能背着一个禾捆跟在大人后面亦步亦趋。
三
作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,汉字携带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,不用发声,后人就能聆听到先祖们的私密耳语。“年”字如此,“岁”字同样如此。与“年”字比起来,“岁”字相对复杂。“岁”早先为“歳”。有人说,“歳”是木星的化身,《尚书·尧典》不是有“历象日月星辰”的记载吗?木星化作“歳”跻身于历法当中。也有一种说法,“歳”字本义是砍断,其形状犹如用大斧斩断人的两只脚,斩断则止步,象征隔断旧时段,开启新日月。无论“歳”字本义是哪种,都在告诉子孙后代,为穿透浑茫天象,先祖在殚精竭虑,探索适宜下种的耕作时机。探索时机后人称作“钦若昊天”,颁布施行则称作“敬授民时”。
阅读《尚书·尧典》时,愚鲁的我不无困惑,为什么“定四时成岁”,就能“允厘百工,庶绩咸熙”?通俗说,为何制定了历法,百官只要尽职尽责,诸多事情就会顺遂兴旺?直到陶寺遗址中那座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复原,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,将岁月转化为播种时机,起直接指导作用的竟是节气。节气早就蕴含于《尚书·尧典》当中,“以殷仲春”“以正仲夏”“以殷仲秋”“以正仲冬”,不仅是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传真,还是“二至、二分”的最早出现。气象学家竺可桢在《天道与人文》一书中指出“二至、二分”为:夏至、冬至,春分、秋分。陶寺观象台正是观测节气的产物。我之所以援引其为证据,是因为该遗址出土文物经过碳十四测定,距今约4300年,对应的历史时段与帝尧时期相仿。这说明,即便《尚书·尧典》中的记载并非当时的文字刻录,也是后人根据前辈口述所还原的世事。
承载着节气的古观象台复原后,屹立在黄土高原上。前往瞻仰,每当远处山头升起的红日穿越观测缝,照亮观测点时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喊:“尧王出来了!”这是我童年养成的习惯。不是我把尧王比喻为太阳,是我故里的父老乡亲一辈一辈对太阳都如此称颂。
当然,我们嘴里的乡音不是“尧王”,而是“耀窝”。在尧都的方言中,“王”字发“窝”音——王村说作“窝村”,王庄说作“窝庄”。乡亲们把尧王比喻为太阳,与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对帝尧“其仁如天,其知如神,就之如日,望之如云”的称颂一致。
帝尧受此尊崇,是因为他分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,前往旸谷、禺谷、交阯、幽都,观察“日月星辰”变化,钦定历法,确定节气,打开了上天的密码。尤其是节气的制定,堪称农事播种的天时路标。我生在尧都,长在尧都,节气农谚熏染着我成长。“惊蛰不耕田,不过三五天”,这是大地解冻的春讯;“白露种高山,寒露种平川”,这是播种小麦的节气。
不过,我的那些乡亲从不说节气,互相言传的都是节令。节令,关于节气的命令。“敬授民时”就是下达农时节气的命令。不违农时,适时下种,才能收成好,衣食足。节气,显然是由“岁”变“年”的重要动力。在历法、节气中,“岁”是初始,尚未实践;“年”是实践后成功的结晶。
年,可谓中华先祖由狩猎向农耕跨越所收获的丰硕成果。
中华民族是感恩的民族,拥有了丰衣足食、安居乐业的大年,也没忘催生大年的岁时节气。至今,岁和年几乎拥有旗鼓相当的地位。倘若有人发问,您多大了?您在人世已经历过60年、70年、80年,回答时却不提年,依然是用帝尧“定四时成岁”的岁,60岁、70岁,或者80岁。岁与年从上古到如今,与国人相依相伴,不弃不离。
岁岁过年,年年守岁。岁岁平安好运来,年年福禄喜盈门。
四
“子曰:大哉尧之为君也!巍巍乎,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。荡荡乎,民无能名焉。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探究中华民族的进程,探究农耕文明的生成,我渐渐将孔夫子的尊崇变成了自己的尊崇。我不仅尊崇帝尧,还尊崇对推进中华文明具有重大贡献的每位先祖。从《尚书·尧典》看,最初以岁的面目出现的年,形成于帝尧时期。不过,这绝对不是突兀而生,而是之前先祖们观测天象的接力长跑,持续发力,代代不懈,终至帝尧时开花结果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:“黄帝使羲和占日,常仪占月。”羲和,应当是羲氏、和氏的总称,由他们观测太阳;常仪也称常羲,负责观测月亮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干脆把羲和神化为太阳的母亲,把常羲神化为月亮的母亲。古人对羲和的想象富有意趣:她与她的十个太阳儿子一起住在东方的扶桑树上。每天都有一个宝贝儿子升空照亮大地,由她驾着龙车把他们送往最高处。每天,每天,从不间断,她是何等尽职尽责,很可能黄帝时期已经委派专职人员负责观测天象,羲和与常羲就是这样的“高管”。高管履职,世代传续,帝尧继位后加大了天象观测力度,高管仍然沿用先前的名称。于是,“乃命羲和,钦若昊天”,羲氏、和氏共同运筹发力,终于“定四时成岁”。
敲击键盘到此处,我仿佛看见一个人撑开竹简,从字行里跳脱出来。他跳脱出的典籍是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,脚一着地即奋力奔跑,追赶太阳。东方曙色初现,朝日尚未升起,他早已起跑。他要赶在太阳离开地面前接近它,逮住它。可惜,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,太阳腾空高升,他未能如愿。他没有泄气,转身朝西追去,想在太阳落下时让理想变为现实。他跑啊,跑啊,再苦,再累,丝毫不敢放慢脚步。气喘吁吁,跑;汗水滴答,跑!然而,终究还是慢了半拍,眼看着太阳在眼前落了下去。他太累了,太渴了。回身饮水,喝干了黄河,不解渴;喝干了渭河,不解渴。他要去北方的大泽喝水,未能赶到,满怀遗憾地渴死了。他不甘心如此失败,倒地前沮丧地抛弃了手杖。手杖成了他理想的化身,居然长成了一片光彩灼灼的桃花林!
这是一个巨人,先民尊称其为“夸父”。这个神话名为“夸父逐日”。我童年、少年都觉得夸父追赶太阳,是自不量力。后来读到了“神农尝百草”,才理解了夸父逐日的内涵。尝百草的神农氏一种一种咀嚼植物,一次一次昏迷,又一次次醒来,终于筛选出了新的食物。从此,先民不再靠单一狩猎维生,开始采摘果实,种植禾粟。中华文明进程,从狩猎到农耕经历了数千年,显然不是一人所能为。足见,神农尝百草是先民塑造出的一个光辉形象代表,体现了不畏生死、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。
倘若说神农氏是在拓展地上的食物种类,那么夸父就是在探索混沌的天象。他要揭示日月变换、冷暖交替的规律,确保有种有收,丰衣足食。夸父虽然宏愿未竟,壮志未酬,但是,他的事业却没有中断。先民们将那片灼灼照人的桃花林作为向往的未来,薪火相传,前赴后继,这才有了帝尧团队探求的成功。
“成岁”,酷似先祖点燃的创新圣火!
五
唐贞观年间,李世民在太极宫饮美酒,赏歌舞,听见远远近近响起了爆竹声,诗兴勃发,挥毫写下《守岁》,有“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”句。千百年来,中国人都把过年作为最为隆重的节日。那么,早先,先民如何欢庆?
《古诗源》中收录有两首诗,隐隐约约透出陈年古风。一首是《击壤歌》: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!”晋代皇甫谧在《帝王世纪》中写道:“帝尧之世,天下大和,百姓无事,壤父年八十余,而击壤于道中。”何为击壤?《风土记》中有解释:“壤者,以木作,前广后锐,长尺三四寸,其形如履。”“先侧一壤于地,遥于三四十步,以手中壤击之,中者为上。”这是先民在做游戏,边唱歌,边击壤,“歌之舞之”。
所有的游戏都有一个前提,必须能够吃饱肚子。研究上古史的专家认为,击壤是先民丰衣足食后欢乐的庆典。欢庆丰收,喜迎未来,虽然朴拙,却是过年的雏形。
另一首诗歌是《伊耆氏蜡辞》:“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意思是,种植靠土地,土壤莫流失;洪水莫泛滥,归回河道里;昆虫别发作,禾苗好生长;草木别入田,安家在沼泽。细细品味,似乎是在祈祷。这就与诗名吻合了,伊耆氏即便不是特指帝尧,也与他相关。帝尧姓伊耆,名放勋。蜡,同“腊”,腊月是古人的祭祀之月。辞,是祭祀时的祷告词。如果说,做击壤游戏是平民广众庆贺丰收,迎接新岁;那《伊耆氏蜡辞》就是官方祭祀天地,祈求丰收。
官方主办新岁庆典,绝不会像民间游戏那么简单。即使那时没有盛大歌舞表演,也会有礼乐仪式助兴。礼乐仪式少不了要有礼器,遥远的帝尧时期有礼器吗?还真有,陶寺文化遗址发掘出了鼍鼓、石磬,还有铜铃。打着鼓,敲着磬,摇着铜铃,吟唱着蜡辞,拙朴而庄重的祭祀大典即圆满礼成了。
这贺岁迎新的开端略显幼稚,却像初生婴儿一样,用勃勃生机,拥抱未来。
六
愿得长如此,年年物候新。
唐朝卢照邻《元日述怀》的诗句,写出了大年的常态化。那大年的常态化起自何时?上溯,再上溯,目光停留处是《诗经·七月》。该诗题为《七月》,诗中的物事却几乎涉及全年的境况。不妨选录翻译出来看看:正月赶着修农具,二月插足把田犁。四月远志开花结籽,五月蝉鸣叫不止。六月展翅纺织娘,七月火星流西方。八月打下树上枣,九月谷场修筑好。十月晒干收进仓,冬月腊月酒斯飨。后续的场景更像过年的写真,先是准备,继而欢庆。“穹窒熏鼠,塞向墐户,磋我妇子,曰为改岁,入此室处。”先民清除垃圾,熏赶老鼠,密封窗户,躲避寒风,准备过年。如何欢庆?“朋酒斯飨,曰杀羔羊,跻彼公堂,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。”献上两杯美酒,宰杀肥美的羔羊,亲朋们欢聚一堂,举杯畅饮,恭祝赐予幸福的天地万物和公侯主管:万寿无疆!
岁时有序,有条不紊。西周时期民众的生产、生活不违农时,衣食无虑,过大年顺理成章。当然读来也有一点不尽兴,寻根大年却没在字里行间见到年字。《诗经》里能觅到年吗?能,而且还是“丰年”:“丰年多黍多稌,亦有高廪,万亿及秭。为酒为醴,烝畀祖妣。以洽百礼,降福孔皆。”其意大致是,丰收年景谷物多,高大粮仓一座座。储存亿万新稻粮,酿成美酒甜又香,献给祖先来品尝。用以祭祀百种礼,普降福禄多吉祥。这首《丰年》,似乎可以看成对《七月》的补充。《七月》聚焦于时序里的生产与生活,《丰年》浓墨重彩活画出了过年风情。仅就祭祀场景看,即呈现了先民敬天法祖的礼仪。“以洽百礼”是敬祀天地万物,“烝畀祖妣”是敬奉先祖。
如果细品,《诗经·唐风》中的《蟋蟀》和《山有枢》,也能感受出过年的滋味。《唐风》流行在古代唐国,唐国是帝尧最早开创的国家。周成王桐叶封弟,也称桐叶封唐,即封在这方熏染着唐尧遗风的大地。
七
天之历数在尔躬,允执其中。
这是帝尧禅让时对虞舜的嘱咐,虞舜禅让时也如此嘱咐大禹。此话口口相传,到了春秋时期,被孔子的弟子录进了《论语·尧曰》。大致意思是帝尧告诫虞舜,你要谨遵躬行天道历法。帝尧为何要如此嘱咐?因为观测天象、形成历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。先祖对上天充满了敬畏。无论是“钦若昊天”,还是“敬授民时”,都不敢胆大妄为,而是遵从天命,不越雷池一步。按规律种植才能丰收,民众才能吃饱饭。这是中华先祖认识天象的准则,也是当时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。
夏朝岁首在农历正月启蛰节气,该是立春。看来虞舜没有忘记帝尧的嘱托,夏禹也没有忘记虞舜的嘱托,对既定历法遵行不二。商朝的岁首则不然,提前了一个月,变为农历十二月。周朝的岁首再提前一个月,变更为农历十一月。战国时期,各国颁布了不同历法,有《黄帝历》《颛顼历》等6种。秦朝奉行《颛顼历》,把十月定为岁首。这一历法与天象不符,难以指导农耕,导致粮食歉收。
何时拨乱反正?西汉颁布的《太初历》,才回归历法本源。元封七年(公元前104年),汉武帝招贤纳士,修订历法。修订结果,由汉武帝选定了邓平与落下闳的《八十一分律历》,重归“正月旦,王者岁首”。规定新年由正月初一始,官方举行盛大朝会、祭祀仪式;民间祭奠祖先、拜贺乡亲。
此后2000多年间,历法虽然屡有变化,但是正月为岁首的根底没有丝毫动摇。大年虽然有正日、岁日、岁旦、元辰、元正、新正、新元等多个名称,但是大年的习俗一脉相承,从未间断。1912年,我国采用公元纪年,将1月1日叫作元旦,将农历正月初一大年改称春节,沿用至今。
大乐与天地同和,大礼与天地同节。中国大年在历史的进程中,日臻完善,荷载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,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盛景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6年02月13日 13版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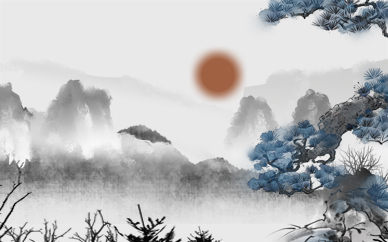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